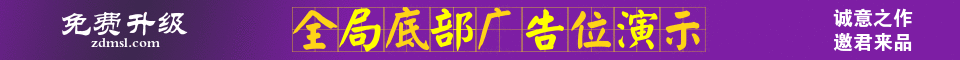的国产创新药 何时拥有自己的 吉利德 跟跑二十年 (的国产创新药有哪些)

过去,我国药品市场以仿制药为主,国产创新药占比很小。近年来,国内制药格局正逐步由仿创结合向自主创新转型。
目前,国内生物医药创新研发活跃,国内更多的创新产品在海外同步临床,更有创新产品在海外同步上市。与此同时,不论是传统药企还是创新药企,整体研发投入的比例和绝对值都不高。此外,创新水平也不够、同质化严重的现象也比较突出。
从一个制药大国转变为一个制药强国,学界、产业界、投资界都有哪些进一步补齐的短板和发展思路?
雷锋网消息,近日,第三届健康产业投融资领袖峰会在北京召开。
峰会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中银国际联合主办。本届峰会主题为“汇聚洞见、引领趋势、智创未来”, 主论坛邀请了多位投资界、医药学界的专业人士进行主题报告,分享并探讨了健康产业的政策变化以及未来的投资发展趋势。

在以《抗周期:创新药投融资前景展望》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中,北京大学药学院院长周德敏,国投创新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肖治,国药投资副总经理刑永刚,鸿运华宁(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景书谦,药渡创始人兼董事长李靖共五位嘉宾,围绕创新药投融资的前景进行交流和讨论,越秀产业基金新医药投资部总经理薛辰担任圆桌讨论主持人。
以下是圆桌讨论的内容,雷锋网做了不变原意的整理与编辑:
从制药大国,到制药强国
薛辰:中国一直是制药大国,如何从一个制药大国到一个制药强国?创新药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产业支柱。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叫做“抗周期:创新药的投融资前景展望”。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周院长,在中国的创新药过程当中,您所在的学校、科室在研发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布局?
周德敏: 我来自北京大学。回北大前,我在美国制药公司工作了很多年。我所在的单位是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由原国家卫计委批准组建的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1985年筹建,1987年12月通过验收并向国内外开放。
实验室的定位是源头创新,这方面我的感触很深。我在美国时观察到,如果一家公司知道另一家公司在做同一件事,一般就不会在这个领域继续下去了。因为它知道对手已经做了好几年,永远赶不上它。所以,美国的制药公司一般都在寻求创新。
而我们国家则是,别的企业不做它也不做,别的企业做它才做,这可能就是最大的不同点。
说到北京大学药学院,大家都知道屠呦呦。那个时代主要是研究从中药里面提取有效成分。到了今天,新药研发则是进入了一个向生物制药跨越的时代。目前,最畅销的药物里面十个有八九个是生物药。
我们国家重点实验室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也做出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
比如,我们跟红杉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要把一种病毒直接变成疫苗。没有感染流感病毒时,它就是预防性的疫苗;如果已经感染,就是一种治疗的药。昨天在基金委介绍这个工作的后续时,也让基金委眼前一亮。
薛辰:之前听说过,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希望孵化出中国的Genentech、吉利德,也想请您分享一下具体的故事。
周德敏: 在斯坦福大学的对面,有两家公司拉开了生物医药时代的序幕。一个是Genentech,一个是吉利德。
吉利德是由一个29岁的化学家和美国前国防部长一起建立的公司,产品大家都很清楚——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抗流感的达菲等,都是从这个公司发展起来。
我经常跟政府部门的领导说,他们自己是大有可为的。作为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在五十多岁时投入自己的精力,成立了可以成为一代传奇的吉利德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Genentech。从生物医药角度来总结这家公司如何投资、创业,有两个关键点:坚实的科学力量和灵巧的商业运作。
Genentech成立于1976年,利用了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伊尔教授(Herbert Boyer)发现的DNA重组技术。这个技术发表以后,被一个非常关注科学领域的27岁投资商注意到。他感觉这里面有潜力,于是再三约请和博伊尔教授见面,后来他们就一起成立了Genentech。
薛辰:创新药研制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不光红杉和鼎晖的美元基金,也希望有机会多接触一下中资的基金。国药投资和国投创新有哪些成功案例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各自有哪些优势?
肖治 :我是国投创新的肖治,目前接管了1100亿左右人民币基金。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基金,主要投资三个方向:生命大健康、智能制造和新能源汽车。我和18个同事一起负责高端医疗器械和创新药这个板块。
真正开始大规模投资大健康领域是在2015年之后。2009年之后,中国有大量海归人才回国研究创新药,并在2010年后不断有成果出来,我们赶上了这个时候。
我们在上一个五年投资了信达、亚盛、康希诺、沛嘉,目前均已在上海上市。除了这些已经上市的企业,过去这五年,我们在生命大健康领域投资了60多亿人民币,共20多个项目。整体偏中后期投资,单笔投资额在2亿人民币以上。
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投资。例如,我们会与一些大的上市公司合作,将其中的创新药板块重新孵化出一家新公司。2017年,我们把阿斯利康在上海的研究院进行了私有化。前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ICC)负责人张小林博士,从职业打工人变身成创业企业家。我们和阿斯利康拿出了现金和资产,变成创新性企业公司。
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我们也投资了像沛嘉这样的公司。
我们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基金,也在不断地摸索探讨,观察2020年疫情之后如何在行业里面进行投资。
过去十年,生命大健康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既有监管政策方面,也有市场资金的变化,更有人才和新技术的变化。所以,和团队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始终会讲一句话:未来投资的很多领域,可能都不会像生命大健康这样一直会蓬勃发展下去。
邢永刚: 我来自国药集团,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国药集团是国资委里唯一一家以医药大健康为主业的央企。国药集团的整体方向是医药大健康,底下产业非常全,是医药健康行业全产业链的一家公司和平台。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坚持打造医药大健康行业的全产业链、全生态链的医药大健康产业平台。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国药集团最早和外资企业进行合作。当时谈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是建国饭店,同时谈的一家制药企业就是国药跟日本一家企业合资建立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国药在投资领域里面有着非常早的经验。当时,还是以国家医药局为主导的投资。
如今,无论是人才,还是产业链布局,国药都培养了很多行业人员。
我在国药待了二十年,一直在法律部工作,公司投资并购的过程几乎是全程参与。我在法律部的工作也见证了医药行业,特别是投融资领域的发展和成长。
现在,我在中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这是国药集团的全资二级公司,所有资金都是集团的,都是国家的钱。与同样是投资行业的同事相比,募资的压力几乎不存在,这是我们的优势。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投资平台呢?
最早进行投融资时,国药集团主要是以控股为主。近几年,我们看到了行业里的新生力量,也考虑到了机制的问题。
设立中国医药投资公司,主要是进行参股,可以采用非控股的方式。我们有自有资金和国药的资源,能够陪着行业的创新者一起成长。我们是可以陪着你们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战斗的投资人。
薛辰:投资新医药项目时,每个机构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有些机构、投资人关注企业的爆发力,有些则是关注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成长稳定性。我想请教一下肖总和邢总,两位所在机构的投资风格倾向哪种?
肖治: 每个基金的特性都不一样,导致投资风格不一样。我们的心态比较平衡,对短期价格的敏感性没有那么高,更关注项目的可持续成长和后劲。
所以,我们在看医药项目时,更关注团队和技术平台,以及未来不断推出新产品线的能力。在药物领域,我们对是不是行业第一名并没有那么关注。我知道,很多机构是希望在一个细分领域,甚至是一个靶点上投的都是A+,我们则是会偏后面一点。
从小变大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药企的锐劲在下降。它不可能永远追求靶点上的中心,反而会相对地追求确定性。我们很多时候看小企业的项目,是希望它们能做出自己的特色。
全球20强药企确实在很多领域中有自己的原创和研究。但越来越多的大型药企会把早期的吸引性研发给小公司,然后通过自己的平台,统一自己的EDM销售,把有确定性的、能够达到10亿美元的大项目做起来,通过组合拳去占领市场。
我们对所投公司的可持续性、团队的平台研发能力更看重,不像一般的投资机构那样希望投资一个业内翘楚的科学家,我们更希望投的是科学家团队。因为我们单笔投资比较大,所以考虑的点可能就和VC类(风险投资)的公司不太一样。
邢永刚: 所有企业的经营都有风险。说到创新药,这是创新领域里面风险最大的一个。但无论是资本方还是创新者,大家都在跟风险赛跑,看谁风险掌控得好。风险是一个底层事物,我们评判的重点是可以在这个底层上走多远。因此,我们更看重跟大家一起“结婚”,一起共同成长,一起慢慢变老,我们对人的判断上,更看重一些。
中国新药研发的“卡脖子”问题
薛辰:投资医药的人都知道“新药风险守恒定律”。投资人要学习这样的定律,同时要学会使用这样的定律。请问一下两位产业人士对新药风险守恒定律怎么看?如果说要对医药投资人进行建议,怎么用好这个定律?
景书谦: 我是80年代初出国学习,在国外读完博士以后就在两家公司做了很长时间的新药研究和开发。首先是在BMS(Bristol-Myers Squibb),然后到Amgen(美国安进公司),Amgen是行业的老大。我在这两家公司做了将近20年的新药研究,也做了后期的开发工作。2010年离开Amgen回国创业,在杭州建立了现在的公司,鸿运华宁生物医药。
我和团队的背景是以开发抗体新药为主,定位是原创新药的研究和开发,当时这个方向与国内较热门的领域不太相合。我们主要专注于一些大型慢病,比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以及肥胖等等这一类疾病。
现在公司有一百多位员工、十几位海归。这些海归大部分都有二、三十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验,基本上都在国际知名药企进行新药研究和开发,一百多位员工里50%以上都有硕士和博士学位。
经过十年的努力,我们打造了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平台。比如首先打破全球瓶颈的G蛋白偶联受体(GPCR)这类靶点的抗周期药研究开发的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基础上,我们的产品线也非常丰富,有二十多个不同的项目,有四个处于临床阶段。
这几个临床阶段的项目可能会在近期进入上市、注册申报阶段,另外还有九个不同的临床前的项目。总体来讲,经过一段时间艰难的摸索探讨后,现在可以说是站住脚了。
我觉得做新药,尤其是创新药,从谋划的时候就一定要想到将来,就是我们常说的“以终为始”。不但要考虑到将来成功的几率,更要考虑到成功以后是不是能满足未来时间点的患者需求。进一步讲,只有满足需求才能在市场占有份额。
其次,在产品的更新换代上。企业选择一些项目后,要定时对项目布局进行规划,不断地更新。参考手机行业的华为、苹果的迭代速度,做医药也应该如此。
李靖: 我是药渡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药渡是做医药大数据,涵盖药物、医疗器械、中医药投资等。平台用户有几十万人,中国的付费用户也超过了五六百家。2006年我回到中国,建立药渡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数据。
对投资人来说,如果对下一个五年、下一个十年的预判不准确,就没办法进行投资。
我们将新药研发比喻为在一个赛道奔跑的雪球,中国的第一个阶段就叫做“远远地跟”,这里有很多例子,比如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就是“远远地跟”。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基本上都是“远远地跟”。
到2019年、2020年就要“近近地跟”,再过十年才能“平行地跑”,再过十年,随着自然科学的全面爆发,才涉及到“领跑”。我自己是“奔跑”的合伙人,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近近地跟”。同事们问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卡脖子”的究竟在什么地方?
中国技术的“卡脖子”主要是集中在筛选方法和动物的模型。为什么“远远地跟”?因为你没有方法,没有模型,一定要等人家写成书发表以后到你这里做ABC动物模型。
直到现在,中国基本上仍然没有在动物模型和筛选方法上实现零突破。 所以第一个阶段之所以是“远远地跟”,是因为新药研发是西方搞的,我们刚进入这个领域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会发现“近近地跟”很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挖掘的话,零零散散的信息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怎么筛选的问题。
“平行地跟”近期肯定是看不到的,“平行地跟”需要自己有想法,这个还需要再十年的时间。
李进教授讲,中国都集中在PD-1单抗领域,为什么大家都集中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信息极度缺乏的表现。 因为没有信息,那只能集中,你做我也做。
做PD-1有三个好处:筛选的可溶量有人可以做、筛选的方法变化有人做、表达有人做。
什么地方限制了想象力?信息的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因为没有信息链和信息,这是很痛苦的。但大家不可能每年都有信息,这样的话就容易形成扎堆。
现在回来谈药物研发的三大定律。一是假如治疗的领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创新药都无法和同机制仿制药竞争,理论和实际当中都无法竞争;二是任何一个me-too药物都不能和first-in-class带有的马太效应竞争。
在赛道里中国的第一个阶段要“远远地跑”,但现在“远远地跑”不行了,我们都是高度的集中,那些药都上市了,我们现在要走近了跑。“远远地跑”和“走近地跑”里面,第一个例子是恒瑞的阿帕替尼。恒瑞的临床提到了研究胃癌,所以阿帕替尼是“远远地跑”,是同样适应症的两个分支,没有竞争。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假如你是“远远地跑”或“近近地跑”,要做中国人的适应症。因为你不可能和它“平行跑”,外国的公司也不可能做中国人的适应症,做中国人的适应症需要每天梳理、推送大量文献。
为什么PD-1的下游组只有加科思在做?又是信息的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相关信息肯定能搜索出来,假如你有这个信息,也可以做一个。这证明了中国人做的比较出名的POC(point-of-care)还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还是“远远地跑”,还是跑的人家的适应症。
既然我们避不开这个阶段,好多人说我们能不能做原始创新?出发点很好,但不现实。任何一笔投资一定有回报的要求。但是我们在“近近地跑”的时候有两个要求:
一是要跑得足够近,需要有非常强的团队执行能力;二是需要大量系统性的信息。全世界有两万多种病种,中国有多少流行病学我们不愿意梳理,人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信息上的贫乏和懒惰导致我们没有出口。
我们一定要走中国的适应症。过去我们对数据认识不充分,以后就要天天看数据,看好了再行动。
薛辰:感谢李总在医药大数据方面的分享。这一期圆桌论坛的主题是《抗周期:创新药投融资前景展望》,创新药投资是一件高风险、高收益的事情,甚至很多人说这跟赌没什么区别。这点想听听产业、学界以及投资界专家的观点。
李靖: 投资分大企业和小企业, 全世界永远不变的规律就是 大求稳、小求新 。恒瑞做me-too药物,我觉得也挺好。它是对渠道的创新,me-too就够了。小公司为什么求新?小公司要革老大的命,所以求新。它的属性是小求新,有五六七八个成果,这样的公司在下一个十年中一定会胜出。
景书谦: 从任何一个方面讲,行业最关键的属性就是要满足患者的需求。需求决定一切,包括怎么布局、研究方向。从国内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我们的收入在增高、预期寿命在延长,将来大健康的维护和管理肯定是发展的大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第二个是行业的发展能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也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创新不是一味坚持做first-in-class,全球做出来的也不过几百个,患者真正需要的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创新、发展方向都应该以患者的需求,作为最重要的落脚点。
邢永刚: 我非常赞成专家的观点。所有的创新价值在哪,新药的落脚点一定是患者和医生。患者是最终端的使用者,而能不能帮助患者减轻缓解症状、进行手术,医生也是一个落脚点。
从产业投资者的角度,我们有两个感觉。
第一,我们自己有科研单位,包括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同时我们也是河北制药的股东以及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在看不同机制下的创新时,我们自己也有非常明确的感觉。
较小的、市场化能力更新的创新者,客观上会起到革新大的、老的研究团队的作用,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 他们通过自己的研发部门去进行研究,通过并购去收购重要的药物,都是两条路同时走。国药也一样,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同时也要在市场上去找真正有价值、能创新的创新药和团队。
我总结一点,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以患者为最终的落脚点。
第二,既然是市场化的,就要让市场去检验。很多科研人员看自己的产品跟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怎么看怎么漂亮,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孩子也就那样。怎么才是好的孩子,要放到市场上去。
肖治: 资本市场是有周期的,这个周期每几年就会到来一次。现在生物医药行业、医疗健康大行业的投资和创业热潮非常高涨,但这个高涨是否可以无限地持续,这是需要大家非常冷静地去看待的。
从2018年开始,我们就对很多项目进行估值,对他们的表现持冷静态度。但是,资本市场不断地开放,带给生物医药领域企业各种机会,我觉得这种热潮一直在延续。但过了2020年,这个热潮是否能一直持续下去,需要在座的各位去思考。
从投资的角度看,我比较认同这样的观点: 中国很快会像美国市场一样,项目上来以后退出很难,而且上去之后再融资的能力也会发生问题, 甚至企业的经营也会出现困难。这个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在中国出现。
我建议各位,在看到中国第一大朝阳行业的各种机会时,也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审时度势地判断每个项目的价值。
周德敏: 去年到今年,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卡脖子”技术。去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教育部到科技部、科学院、工程院都要求我们调研一下哪些是“卡脖子”技术。
我觉得说得清、说得出的都不是“卡脖子”技术 。因为说得出来的,你再做也就是me-too。真正“卡脖子”的是未来的,是无形的。美国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做调研,对未来二十年到三十年能够产业化、能够代表未来方向的技术进行出口管制。
我特别关注了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限制访问学者的各个领域,在这里面生物医药未来的“卡脖子”技术就是生物技术,美国将这个技术列为第一个,人工智能、芯片等都是放在最后。我认为,生物技术就是未来可以真正在生物医药上实现突破的,比如说该领域的 生物纳米材料、合成生物学、功能基因组学和神经科学。
中国人要在这方面实现真正的创新不容易。因为这跟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
所以,我希望投资界的同仁,可以通过你们的杠杆作用倒逼大学和教育业,在生物技术的源头上去做真正的创新。口头上说容易,真正去做是很难的。但我相信。投资和资本市场有这种能力来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
薛辰: 我从北医毕业有八年时间,在国外工作过五年。“关爱生命,呵护健康”这个理念一直萦绕我心。曾经有一家知名跨国药企的sloGAN让我印象深刻:如果药物的研发是以人类健康福祉为目的的,我们相信利润必将随之而来。这样的话也适用于投资人、企业家和学者。中国在新药创新方面的路还有很远,希望大家携手,共同努力,共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原创文章,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详情见 转载须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