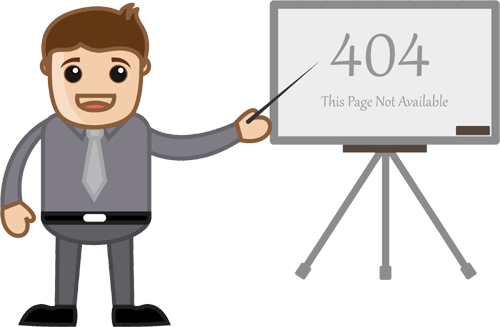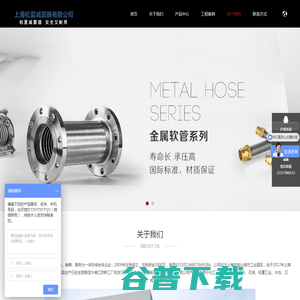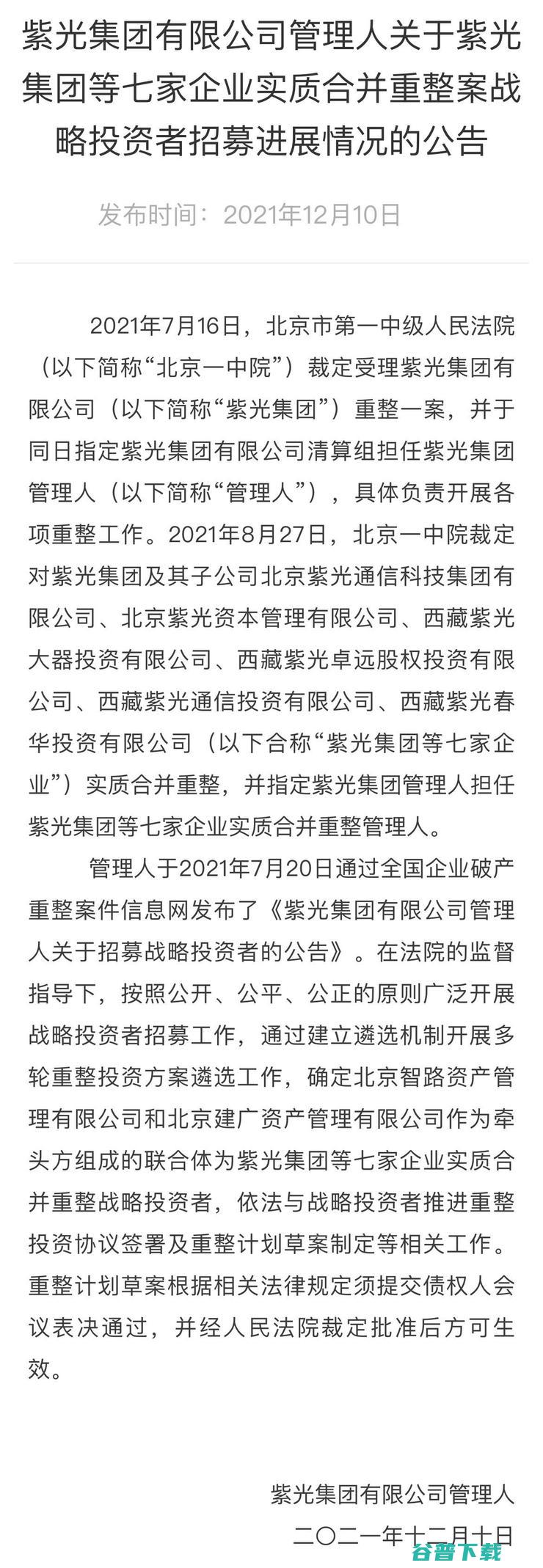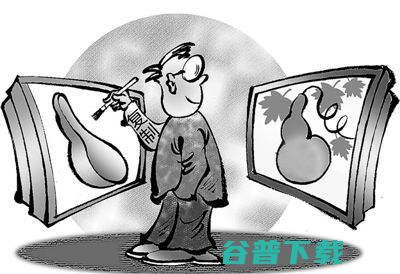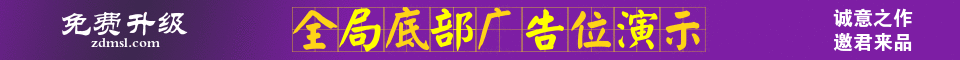近东救援工程处 进入加沙的人道声援处于数月来最低水平 (近东救援工程招标公告)
联结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援和工程处(近东救援工程处)12日正告称,目前, 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声援严重无余,特意是加沙地带北部地域 。

美国10月致信以色列,需要以方在11月13日前采取措施,改善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状况。在被问及截止日期来到前状况能否有所改善时,近东救援工程处官员沃特里奇说,理想上, 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声援处于数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0月,平均每天仅有37辆载有人道主义声援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地带。在加沙地带北部,外地民众濒临饥馑,而且状况时辰都在变得“愈加严格”。联结国方面进入加沙地带北部的恳求也一再被拒绝。
拉法口岸地图位置
拉法口岸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南部与埃及交界处,是巴勒斯坦不用经过以色列而直接通往外部世界的口岸。
根据巴以双方2005年11月15日达成的协议,欧盟将派安全人员对拉法口岸进行监督,以色列将通过电子监视器远程监视口岸人员进出情况。 这一天,让他们足足等了38年。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21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第一批载有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20辆卡车开始通过拉法口岸过境点,前往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卡车将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仓库卸货,随后分发给加沙地区各个医院。 2005年11月26日正式开始处理进、出关业务。 该口岸初期每天开放4小时,以后逐步增加到全天候开放。
拉法口岸区位环境介绍:
以色列在2010年5月底袭击了驶往加沙地带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并造成伤亡后,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命令无限期地开放与加沙地带接壤的拉法口岸。
在拉法和埃及接壤处,挖掘有数百条地道,由于以色列的封锁,这些通道主要用于向加沙走私生活物资。 像阿萨姆这样通过走私通道进出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由于通过地道走私属于非法行为,且地道经常发生坍塌事故或者遭到以色列的轰炸,非常危险,所以大多数加沙居民还是选择通过合法手续经口岸出入。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百科-拉法口岸
加沙地带的英文名是什么?
加沙地带 Gaza Strip 亦译加萨走廊,阿拉伯语:قطاع غزة或Qita Ghazzah;希伯来语:רצועת עזה或Rezuat Azza西奈半岛东北部地中海沿岸占地363平方公里(140平方里)的区域。 加沙走廊与众不同的是,以其人口稠密的居住区而未被承认是现存的任何国家的合法领地。 加沙地带(阿拉伯语:قطاع غزة或Qita Ghazzah;希伯来语:רצועת עזה或Rezuat Azza)是一条位于以色列西岸、西奈半岛东北部的狭长地带,主要由巴勒斯坦人聚居。 1948年阿以战争埃及占领,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又再被以色列夺回。 像加沙地带这样人口稠密,但是在法理上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地区,是很不寻常的。 加沙地带69%的土地与西岸的部分地区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其他部分(主要是以色列公民居住的地方)则由以色列管理。 由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允许拥有正规军,治安由巴勒斯坦的公共治安队和民警负责。 2005年2月,以色列政府决定在夏天将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并放弃所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居民点。 撤军后,以色列将依然控制加沙地带的海岸线,以及加沙地带与埃及之间的一个狭长区域。 但以色列国内对撤军计划有很大分歧。 2005年8月15日,以色列关闭加沙古什·卡提夫犹太定居点,正式开始撤出加沙,结束了以色列38年来对加沙的占领。 2007年6月,哈马斯通过加沙之战在法塔赫手中夺得该地的控制权。 [编辑本段]历史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时鄂图曼帝国结束在那里的统治后,加萨走廊成为国际联盟托管的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由英国治理。 在这项托管结束之前,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接受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割巴勒斯坦的计画,其中加萨镇和附近的一片区域被分配给阿拉伯人。 1948年5月15日英国结束托管,而在同一天,第一次以阿战争就开打了。 埃及的军队不久就进入加萨市,那里成了埃及远征军在巴勒斯坦的总部。 由于1948年秋天的激战,在阿拉伯人占据的城镇周围地区缩减为一条狭长的地带,长40公里,宽6∼8公里。 这条地带就被称为加萨走廊。 1949年2月24日在以埃停战协定中画定其界线。 1949∼1956年和1957∼1967年之间,加萨走廊是在埃及的军事统治之下。 从一开始,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居住在肮脏营区里的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生活极为贫困。 埃及政府并没有把这个地区看作是埃及的一部分,而且不准难民成为埃及公民,或移民到埃及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则不许他们回归故土,也不补偿他们所丧失的财产。 难民多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接济。 许多年轻难民变成了「费达因」(fedayeen, 对抗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游击队);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攻击是促成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西奈战役的原因之一,当时以色列人占领了加萨走廊。 1957年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以色列才把加萨走廊交还给埃及。 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里,加萨走廊再度被以色列占领,并在随后的25年里一直占有这块区域。 1987年12月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占领军之间的骚乱和暴力街头冲突象徵了一场起义运动的诞生,称(武装反抗运动)(intifadah, 阿拉伯语意为(摆脱))。 1994年根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所签订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以色列开始阶段性地把加萨走廊政权转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 由阿拉法特所率领的这个初出茅芦的巴勒斯坦政府面临了许多棘手问题,如经济停滞,民众的支持分裂成几个派系,与以色列谈判进一步的撤军和领土权的问题陷入瓶颈,以及好战派的穆斯林团体(如伊斯兰的圣战组织和哈玛斯〔Hamas〕)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拒绝和以色列妥协,并且意图要使和平进程破局。 2000年末期以、巴之间的谈判破裂,接著是爆发更进一步的极端暴力活动,称为第二次或艾克萨(Al-Aqsa)(武装反抗运动)。 努力为停止战斗而奔波的以色列总理夏龙(Ariel Sharon)在2003年晚期宣布了一项针对撤离加萨走廊的以色列士兵和屯垦居民的计画。 2005年9月以色列完全撤离了这个地区,加萨走廊的控制权也移转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过以色列继续在其边界和空域巡逻。 2007年巴勒斯坦的主要政党哈玛斯和法塔赫(Fatah)之间在这里的暴力冲突逐渐升高;冲突的结果是哈玛斯掌控了加萨走廊,而法塔赫领导的紧急内阁控制了西岸。 虽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统默罕默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要求哈玛斯撤出加萨走廊,但哈玛斯仍控制这块地区。 2007年秋,以色列宣布哈玛斯所控制的加萨走廊是一个怀有敌意的实体,并通过一连串的制裁手段(包括切断电力、严格限制进口品和封闭边界)来对付它。 以色列南部住区仍持续遭火箭袭击,2008年1月以色列决定加强制裁措施,完全封锁与加萨走廊的边界,并暂停燃料输入加萨走廊。 1月底,也就是在以色列封锁近一周后,哈玛斯军队破坏加萨走廊与埃及的边界部分围墙(2007年中期哈玛斯接管以后封闭),据估计,有几十万名加萨人穿过这些缺口到埃及抢购食物、燃料和物品等封锁情况下买不到的东西。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暂时答应开放缺口以纾解加萨人民的艰苦状况,之后再开始修复边界。 经过数个月的协商,以色列和哈玛斯终于在2008年6月同意定於下半年实施停战计划,然而,不久之后即因双方互控对方违反规定而破坏了计划。 [编辑本段]人口情况加萨走廊由於人口稠密并不断快速增加(该区人口成长率位居世界前列),生活条件普遍恶劣;供水、下水道和电力设施不足,以及失业率高。 农业是受雇人口的经济主流,有近3/4的土地为耕地。 主要作物是在有水利灌溉的地方种植的柑橘类水果,并且在以色列的安排下外销到欧洲和其他的市场。 也生产专供贩售的作物、小麦和油橄榄。 轻工业和手工艺集中在加萨市,它是本区的主要城镇。 在政局稳定时期,每天有多达1/10的巴勒斯坦人口越过边界到以色列(他们在那里不可以过夜)担任仆役的工作。 政局紧张和暴乱发生时,常使以色列当局延长封闭边界的期限,许多巴勒斯坦人因而失业。 1967年9月进行首度的精确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比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或埃及先前所作的估计为少,而近一半的人口是住在难民营里。 人口约1,444,000(2006)。 约132.5万巴勒斯坦人和八千多名以色列人住在加沙地带,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是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难民或他们的后代。 加沙地带1967年的人口是1948年的接近六倍,此后当地的居民数仍然不断增加。 加沙地带的人口密度相当高,出生率也相当高(平均每个妇女有5.91个孩子),当地深受贫困、失业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所困扰。 1967年开始,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建立了约25个居民点,这些以色列人的人均地面占有,比当地的巴勒斯坦人高得多。 不过,2005年以色列政府决定放弃所有居民点。 加沙地带的人口增长率为4%,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都有很大的家庭。 大多数当地人是穆斯林,少数为基督徒(0.7%)和犹太教徒(0.6%)。 出生率:40.03出生/1000居民(2005年估计数) 死亡率:3.95死亡/1000居民 迁徙率:1.6迁徙者/1000居民 婴儿死亡率:23.54/1000出生 繁殖率:6.04婴儿/妇女 居民增长率:3.83%[编辑本段]地理位置加沙地带位于中东,与埃及接壤的边界长11千米,(拉法就位于边境附近),而与以色列接壤的边界则长约51千米。 保守的犹太人认为加沙地带是以色列的领域,而巴勒斯坦人则声称这是将来要成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领土。 一些以色列人,包括首相阿里埃勒·沙龙打算单方面放弃所有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居民点,这些居民点主要集中于西南边靠海岸的喀什卡提夫。 此外,加沙地带与地中海还有一条约40千米长的海岸线。 但由于以色列的军事管辖,加沙地带对其海岸线没有控制权。 加沙地带气候温和,冬季温暖,夏季则炎热干旱。 地形平坦,有些地方是丘陵,海岸有沙丘。 最高点海拔105米。 自然资源有可耕地(加沙地带约三分之一的地区被灌溉),最近还发现天然气。 环境问题包括沙漠化、淡水咸化、废品处理、饮水不洁带来的疾病、土壤恶化和地下水资源的消耗。 加沙地带被认为是人类摇篮之一。 人类最早的用火遗址是在加沙地带发现,一些最古老的人的化石也是在这里发现的,一些非常古老的抽象符号有可能是人类最老的文字。 [编辑本段]经济状况1994年5月,根据开罗协议,加沙地带的经济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 从1992年到1996年,由于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下政府贪污和管理不良,加上以色列在遭受一系列恐怖袭击后,将加沙地带的边境关闭,期内加沙地带的经济萎缩了三分之一。 在边境关闭前,有许多加沙地带的人到以色列工作。 经济不景导致高失业率。 1998年,以色列改变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开始减轻封锁巴勒斯坦的经济,并减缓对巴勒斯坦货物和劳工运输的限制。 这使经济连续三年恢复。 但2000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武装起义,导致以色列再度封锁。 在此后两年中,巴勒斯坦内部的斗争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摧毁了加沙地带主要的工厂和管理机构,许多企业倒闭,国家总生产力大降,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劳工的收入也大降。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2001年经济下降35%,人均收入为每年625美元。 6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加沙地带的工业主要是小型的家庭企业,其产品为纺织品、肥皂、橄榄树木雕刻和旅游纪念品。 以色列人在一个工业中心建立了一些小型现代化的工业。 电力由以色列提供。 主要的农产品是橄榄、柠檬、蔬菜、牛肉和奶制品。 主要出口柠檬和鲜花,主要进口食品、消耗品和建设物资。 主要的贸易对象为以色列、埃及和西岸。 一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国立阿拉伯巴勒斯坦大学于2002年末为国际援外合作署作的一个研究表明,巴勒斯坦人普遍缺乏营养。 17.5%6岁到59个月的儿童患慢性营养不良,53%的年轻和中年妇女以及44%的儿童患贫血症。 [编辑本段]运输通讯从南到北加沙地带有一条标准轨距的铁路,但已荒废,只有少数轨道保存。 这条铁路过去在南部连接埃及的铁路,在北部连接以色列的铁路系统。 此外,加沙地带还有一个小的、原始的公路网,它唯一的海港是加沙市,现在已被关闭。 加沙国际机场于1998年11月24日开放。 2000年10月被以色列下令关闭,2001年12月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它的跑道。 加沙地带有简陋的电话服务系统,两个电视台(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理),没有广播电台,此外还有四个互联网服务商。 大多数巴勒斯坦家庭拥有收音机和电视机。 [编辑本段]战争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组织的空袭行动截至2008年12月31日,据加沙医疗机构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以军大规模空袭目前至少已造成39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900人受伤,死者中至少有42人为儿童。 以色列空袭了加沙的伊斯兰大学,造成了人员伤亡。 稍后,以色列空军又轰炸了边境城镇杰巴利亚的一座难民营,炸死4人,其中有一名小女孩。 哈马斯前总理哈尼亚的住所也是空袭的目标。 但炸弹没有击中目标,紧挨哈尼亚住宅的一幢房屋被炸毁。 哈尼亚在袭击时没有在家。 南部海岸城镇拉法赫也遭受了空袭。 有兄妹三人在空袭中丧生,其中一名儿童,两名少年。 与此同时,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火箭攻击并造成3名以色列人死亡,射程越发深入以色列境内。 至少一枚火箭打到港口城市阿什杜德附近,在加沙以北大约30公里。
巴勒斯坦入联写100的完美读后感
你好,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句话并不是一种文学隐喻,而是一个数十年来从未停止的真实事件。 这片土地曾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几乎与圣经时代一样的景致,而今则在以色列的推土机下加速消失,荒诞的是,这些人声称自己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景致。 在这里,双方的记忆、历史、情感、诠释与权利重叠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悲怆的画卷。 更多一头山羊和更多一英亩土地 旷日持久的巴以悲剧(它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新闻头条),其主要的症结在于:两个族群对同一片土地提出了相互排斥的主张,而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要求是有充分正当性的。 以色列在尚未立国的移民时代起,就非常注重通过点点滴滴的持续行动来获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法律占有,其开国总统魏茨曼将这一策略形象地描述为“更多一头山羊和更多一英亩土地”。 他们对土地的兴趣几乎达到痴迷的程度,土地就是一切,直到今天,以色列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正式宣布国界的国家。 犹太复国主义者深信,他们是“没有国土的人民”来到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土”。 当地巴勒斯坦人从不被认为有权拥有土地,他们的法律地位多少有点像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土著:虽然他们住在那里,但却不被视为那片土地的主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巴勒斯坦人的悲剧,但他们的声音却很少被外界听到。 作为一个几乎从未离开故乡的巴勒斯坦人,拉贾•舍哈德在这本小册子里记录下了自己数十年来在巴勒斯坦的七次散步,每一次他都发现风景在发生逐渐的、或许是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他也越来越无法自在地漫步了,因为脚下的土地已经被以色列的控制网络割裂成无数碎片。 一个人在自己故乡逐渐丧失行动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控诉。 从他的叙述中也不难看出,巴勒斯坦人无力抵挡以色列人滴水穿石般的推进。 对于这片土地的权利,他们仅有一些泛原则立场,却缺乏有效的手段。 用书中的话说,巴勒斯坦人根本无力开展建设,因为他们“没有路,没有开发,没有建筑。 ……我没见有人做过,也从没见过推土机。 1967年以后,巴勒斯坦需要以色列官方批准才能拥有一台推土机。 ”即使是在西岸这样的巴勒斯坦控制区,以色列也保有所有公路的管辖权,其士兵可以随时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拦截过往的任何车辆。 这小块土地上有500多处以色列的检查站,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想要前往40分钟车程之外的加沙地带,比去中国还难。 就这样,以色列通过密密麻麻的定居点和公路网,点线结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矩阵。 即便巴勒斯坦人掌管着自己的城镇,但连接这些城镇的道路却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从而掌控着巴勒斯坦人的行动,也使得一个巴勒斯坦国根本无法实现事实上的独立,因为它已失去连续和完整。 而这些用以控制巴勒斯坦的定居点和道路,事实上绝大多分都是巴勒斯坦的劳动力帮助修建的,因为这些绝望的失业青年不得不依靠以色列提供的工作机会来谋生,即便那是在给自己修建铁笼。 以色列的定居点有公路网和隧道与以色列本土相连,而巴勒斯坦居民想走动则必须通过一系列军事关卡,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 平心而论,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人相比,生活不算最差,但他们所受的屈辱最甚。 以色列的将军和内阁大臣公开谈论要把他们“像瓶子里被麻醉的蟑螂”一样控制出来,是这片土地上有待清除的“阿拉伯毒瘤”。 正如舍哈德在数次漫步中日渐感到的,“现在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要秘密行动,像不受欢迎的陌生人,烦恼不断,从不感到安全。 我们变成了大以色列的临时居民,生活在以色列的宽容下,在控制检查站的年轻男女士兵手下遭受侮辱的对待,他们随意决定是让我们等上几个小时,还是放我们过去。 ” 这样,在巴勒斯坦人记忆中的故乡逐渐陌生,大地被按照以色列人的意志重新塑造,以符合他们对圣地的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熟悉的景致的消失几乎是一种宿命。 多年前贝鲁特战乱后,托马斯•弗里德曼曾问一个当地老人:原来的房子在哪?老人答:你们的车正在它上面驶过。 那么这里的人呢?答:你们也可能正在一些人上面驶过。 最惨痛的记忆莫过于此。 景观失忆 以色列立国以后就持续不断地推进一项计划:将当地的阿拉伯语地名用希伯来语重新命名。 1949年7月,总理本-古里安亲自监督,下令在两年内为全国“所有地方,所有山脉、河谷、泉水及道路等冠以希伯来名”,这被左翼史学家称为“抹杀记忆”行动。 鉴于许多巴勒斯坦人已逃离家园,城镇和村庄被毁,连地名也重新命名,因此,在多年之后,当地的原有阿拉伯痕迹将荡然无存。 这一行动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犹太人对圣经和圣地的想象,重塑地表。 中世纪的十字军也曾试图真实再现古代圣所的设计和布局,这些持续不断的游客和朝圣者不断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塑造他们心目中的圣地。 舍哈德正确地意识到,“也许巴勒斯坦灾难的根源就在于它是西方历史和圣经的想象中心”,因为这些外来者眼里看到的并非现实中的当地风景和居民,而是与他们自己头脑中的幻象与图景相符的土地。 这样,“再造出圣经般的如画的风景,成了对这片土地拥有古老权利的证明”。 他忍不住讽刺道,自己的故乡拉马拉之所以幸运逃过一劫,原因就在于它并未在《圣经》中被提及过。 在他的历次散步中,不断地记录和回忆着这片土地原有的风景:梯田、橄榄园、石头建筑和家畜,这是他们世代在此居住的世界本身——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他们居住权的证明。 他不断重申:自己一度曾熟悉的这些山冈大地,正在变得面目全非。 这几乎像是一种“失乐园”般的伤感:那个“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会感到熟悉的圣经风景”(这是大部分桃花源世界的特征:静止性)、那片原本让人宁静和自由的土地,已经再也不会回归原貌,而自己却不幸要目睹这一切。 在这荒原中漫步、回忆、记录,这确实是一件孤独的事,何况他的大声呐喊,面对的是“听不见我声音的世界”。 巴勒斯坦村民不习惯悠闲地散步,以至于一个以色列士兵对他说“我怀疑你是阿拉伯人,但不确定。 阿拉伯人不散步的。 ”两人由此展开漫长的对话,在这里,双方立场的歧异暴露无遗。 在这个以色列士兵看来,以色列将附近土地划为自然保护区,是一件有益的事,“如果没有我们它就会被破坏。 作为一个漫步者,你应该感激。 ”而在舍哈德看来,这却是荒谬的:“你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现在像主人一样在这里散步,而我却像罪犯一样在少数受控制的小路上走。 ”何况在他记忆中,以色列人到来之前的这片谷地才真正是一个乐园。 这触及到了一个景观地理学上的一个根本问题:“景观的含义就是谁有权力表征景观的功能。 ”看起来只是双方对景观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则是话语权和记忆的争夺。 舍哈德之所以要将漫步中的所见到的“正在消失的风景”记录下来,他内心最恐惧的也许是“景观失忆”——由于景观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变化,数十年后人们将不再记得它当初的样子。 连一点记忆都没有给巴勒斯坦人留下之后,这片大地也就将不再为他们所有,就好像巴勒斯坦人从未在此生活过一样。 这如何是可能的?两个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群,却没有任何共同的叙事,连共享普通生活也不可想象,双方都死守着自己的记忆,而盼望着对方彻底遗忘。 在最后一次散步时,舍哈德已经明显丧失希望:“很长时间我都不会再回到这里了。 在我有生之年,也许在和以色列可恶的冲突及其所有后果结束之前,我不会再来了。 ”然而真的应该如此绝望吗?这本书本身就可以成为抵抗,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一部分事实已经遗失。 而陈述是我们仅有的一切。 ”记忆和陈述,本身就是最难泯灭的希望。